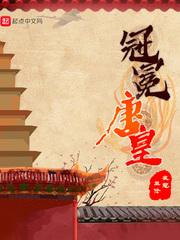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夜无疆 > 第548章 梦寐以求(第2页)
第548章 梦寐以求(第2页)
老妇人点点头,指向身后一口枯井:“每天傍晚,风穿过井口的时候,就会哼起来。起初我们以为是幻觉,可后来连狗都不叫了,它们也听得入神。”
云启走向那口井。
井壁斑驳,爬满岁月刻痕。他俯身倾听,耳畔只有呼啸风声。正欲退开,忽然??
一阵极轻的旋律自深处升起。
>“月亮走,我也走……”
音调断续,却被风托着,一圈圈盘旋而上,如同灵魂低语。
他闭上眼,任那歌声流入心间。刹那间,识海震动,玉光在胸前隐隐发热。他看见无数画面闪现:一群孩子围坐在篝火旁,听着祖母讲述祖先迁徙的故事;一对恋人躲在沙枣树下,许下永不分离的誓言;一位老人临终前握住孙儿的手,将家族信物交予他,眼中含泪却微笑……
这些都不是他的记忆。
但它们真实存在。
“原来如此……”他喃喃道,“你们一直在说话,只是没人愿意听。”
就在这时,地面轻轻一震。
不是地震,而是一种柔和的共振,从地底深处传来,顺着脚心直抵脑海。云启猛然睁眼,发现四周景象已变??夜幕降临,星空璀璨,而每一颗星辰之下,竟都浮现出一道半透明的人影。他们或坐或立,或笑或泣,皆面向绿洲中央,仿佛在等待什么。
老妇人不知何时来到他身旁,轻声道:“这是我们死去的人。三十年前大旱,死了很多人。我们把他们的名字刻在陶片上,埋进沙里。没想到……现在他们都回来了。”
“不是回来。”云启望着满天虚影,声音轻得像怕惊扰梦境,“是你们终于愿意想起他们了。”
那一夜,云启留在绿洲。
他没有使用任何设备,也没有试图记录数据。他只是坐在篝火旁,听人们讲过去的事,讲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悲欢。有个少年说起自己从未见过的父亲,在战争中失踪;一位母亲低声诉说夭折的女儿,每年生日都会在窗台放一朵野花;还有位老兵,颤抖着掏出一张泛黄照片,上面是他战死的兄弟,两人穿着旧式军装,笑容灿烂如春阳。
每一段话语落下,空中的人影便清晰一分。
到了午夜,童谣再次响起。
这一次,不再是风中的呢喃。
是从每一个人的心底,自发涌出的合唱。
>“月亮走,我也走,妈妈背我去看星斗……”
歌声温柔而坚定,穿透沙尘,直上云霄。云启仰头望去,只见星河翻涌,万千亡魂随之轻摆,宛如随风起舞的萤火。而在最明亮的那颗星辰之下,一道熟悉的身影缓缓浮现。
白色长裙,黑发披肩,眉眼温润如初。
阿念。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他,嘴角带着浅笑。
云启站起身,喉头哽咽,终究只唤出一个字:“……阿念。”
她伸出手,似想触碰他,却又在半空停住。然后,她转身,指向远方的地平线。在那里,一道极光正悄然升起,形状如桥,横跨天地。
下一瞬,她消散在星光之中。
云启跪倒在地,泪水无声滑落。
他知道,那不是幻觉,也不是共感投影。那是千万思念汇聚成的一瞬真实??当所有人都愿意记住一个人时,她就不会真正离去。
---
十日之后,北境主控室再度召开紧急会议。
苏璃将一段新采集的数据投射至中央屏幕:西漠绿洲周边三百公里范围内,地脉中的共感频率已形成稳定循环,且正以每日五公里的速度向外扩散。更惊人的是,沿途所经之处,所有未接入网络的村落均出现了类似现象??亡者影像重现,集体梦境同步,甚至有人声称与已故亲人对话长达数小时。
“这不是技术扩散。”陈渊盯着图表,神情复杂,“这是文化觉醒。人们开始重新定义‘死亡’,不再将其视为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共存。”
“可这也带来了风险。”苏璃指着几处红色警报区,“某些极端组织已经开始利用这种现象制造信仰崇拜。他们在偏远地区宣称‘神明降临’,要求信徒献祭情感以换取‘永生通灵’。已经有三起群体性精神崩溃事件上报。”
执刃冷声道:“这些人不是在传播希望,是在贩卖恐惧。他们利用人们对失去的痛,编织新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