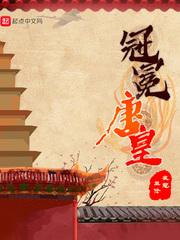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744章 他从来不吃醋你不了解他(第1页)
第744章 他从来不吃醋你不了解他(第1页)
这个小意外,许靖央没有放在心上。
她对阿柳吩咐:“若惊吓了今日的茶客,今日所有茶钱都记在本王账上。”
待出了茶楼,寒风凛冽,许靖央看向景王,微微拱手。
“王爷其实不必如此出气,只怕皇上会怪罪。”
许靖央知道,景王是故意下了狠手。
景王淡淡一笑,比那风雪还要淡漠。
“昭武王,本王跟你不同,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害怕被罚。”
许靖央轻轻点了点头。
景王又说:“何况,被她当众指着鼻子说我们有奸情,若二哥知道,饶。。。。。。
夜雨复临,檐下铜铃再响,却比往日清亮三分。阿芜立于天听院最高处的观星台,手中捧着一卷新制玉简,其上刻录的是由十七座回声井共鸣还原出的《女官列传》残篇。字迹如活水流动,在月光下泛起淡淡银辉??这是言脉系统全面复苏后的第一份成果,也是三百年前被焚毁的“百名女学士名录”中唯一幸存的部分。
她指尖轻抚过那些名字:苏清漪、林婉儿、陈小砚、裴若兰……每一个都曾真实存在,却被史册抹去。如今,她们的名字不仅重现人间,更在承言碑上燃起了不灭之火。
春芽悄然登台,肩披薄毯。“风寒露重,院长该歇了。”她低声说,“明日还要主持‘言种学堂’开典,陛下亲赐匾额,礼部尚书也会到场。”
阿芜摇头:“我睡不着。你知道吗?昨夜我梦见母亲站在太庙前,手里拿着一本没有封面的书。她问我:‘你可记得我们为何而战?’我还未答,钟声就响了,满殿香雾弥漫,她便消失了。”
春芽沉默片刻,道:“或许她是想提醒您??胜利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阿芜闭目,深吸一口气。的确,裴元昭虽已伏法,但他的思想并未死去。朝中仍有大臣暗中抵制女子参政,民间更有流言称“妇人干政,国将不宁”。更有甚者,竟伪造诏书,假借皇帝名义发布禁令,试图关闭各地新设的女子书院。
“今日早朝,户部侍郎李崇安又提‘女子无嗣则不可承爵’之议,要求收回已授功臣遗女的世袭资格。”春芽递上一份密报,“他还联合宗正寺,欲以‘悖逆祖制’为由,弹劾您擅自重启言脉系统。”
阿芜冷笑:“他们怕的不是制度改变,而是记忆觉醒。一旦每个女子都能听见先辈的声音,谁还信他们那一套‘天生卑弱’的鬼话?”
她转身走入内殿,取出那枚从西域带回的水晶铃舌。此刻它通体透明,内部却浮现出无数细小光点,宛如星辰流转。这是沈知微最后留下的“声核”,凝聚了她一生的记忆与意志,唯有血脉至亲方可激活。
阿芜割破指尖,将血滴于铃心。刹那间,一道清音自水晶中荡出,直透地底。承言碑剧烈震动,碑面裂开一道缝隙,从中升起一座微型石台,台上赫然陈列着七枚青铜符牌??正是《言脉七关》所对应的**言权信物**!
“原来如此……”阿芜喃喃,“这七块符牌,才是开启真正权力的钥匙。前四关靠抗争打破,第五关要靠制度确立,而这最后两关??第六、第七,必须通过祭祀与传承,让女子之名正式进入宗法体系。”
春芽骇然:“您是说……我们要改族谱?要让女儿也能入祠堂?”
“不止。”阿芜目光坚定,“我要让天下每一座宗祠,都设立‘女子功德位’,凡有功于家国者,无论男女,皆可受祭。否则,所谓的平权,不过是空中楼阁。”
两人正商议间,忽闻外头急促脚步声。林婉儿浑身湿透闯入,手中紧攥一封火漆密函。“敦煌急报!”她喘息道,“乌孙石窟遗址再度异动!沙丘之下传出吟诵声,昼夜不息,方圆十里百姓皆闻女子齐唱《召灵谣》!更有牧民看见夜空浮现巨大光影,似千百女子执灯行走于云中!”
阿芜瞳孔一缩。那是言脉系统的自我修复机制在运作??当足够多的记忆被唤醒,亡魂便会自发聚合,形成集体意识投影。
“他们回来了。”她轻声道,“不是幻象,是历史本身在反抗遗忘。”
翌日清晨,太极殿前鼓乐齐鸣。金色匾额高悬梁上,上书四个大字:“言种启明”。
文武百官列班而立,百姓挤满宫门之外。皇帝端坐龙椅,神情复杂。他知道,今日这一幕,或将彻底改写王朝根基。
阿芜身着玄底金纹长袍,缓步登台。这不是官服,而是仿照沈知微当年统军时所穿的“女帅礼甲”改制而成,象征军功与学问的双重继承。
她开口,声音经由特制音镂装置传遍全城:
>“今日开典,并非庆典,而是一场审判??对三百年谎言的清算,对千万沉默灵魂的告慰。”
>“我们不要施舍,不要怜悯,只要一个最简单的权利:**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