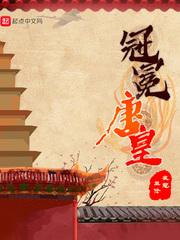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猛兽隔离区(校园1v1) > 82默许(第2页)
82默许(第2页)
勒得倪亦南快要喘不过气,她小小挣了一下,食指停留在他臂弯转折处,那条长长的,像刀疤形状的软肉上。
那是纹身的位置。
动作顿了两秒,蓦地想起邬霜影的话。
倪亦南:“你这里怎么了?”
“不小心划到。”
倪亦南深吸口气,咬着字音:“。。。。。。还在骗我!”
真的生气了。
挣开他抬脚回房间。
沉迦宴拧了下眉,把人拽回来,手臂撑在两侧,将人围困在琉璃台前。
他沉默地注视她,话语在喉间来回翻滚、斟酌。
半晌。
“我爸为了让我留在墨尔本,切断我和外界所有联系,雇了十多个保镖监视我。”
“一月份,我和保镖发生肢体碰撞,不小心划到。”
“就是这样。”
说一半瞒一半,惊心动魄的画面被他一带而过,语气淡得仿佛不是在说自己。
倪亦南知道他故意的。
“那你腿呢?”
“也是那个时候——”沉迦宴话锋一转,不以为意道,“小伤,早好了。”
“小?”
倪亦南眼眸清润,在黑暗中透着微光,一眨不眨执拗地望着他
沉迦宴偏开眼,“骨折而已。”
“。。。。。。而已。”
邬霜影说他是粉碎性骨折,没有送去医院包扎没有接受治疗,当晚直接被推上飞机。
江城到墨尔本,十多小时的航程,就那样硬生生扛下来吗。
对方有多少人,他只有一个人吗,缝了多少针,有没有别的伤,有没有后遗症,阴雨天会不会痛。。。。。。
倪亦南忍不住去想象他经历的疼痛。
疼痛的程度,疼痛的画面,疼痛的感受,疼痛的无助感。
鼻尖酸涩,喉咙变得厚重,连吞咽都十分费力。
末了,她偏开脸,垂下眼,盯向他身后的白墙。
眼中的微光汇聚成一小束,变成一串串圆润剔透的珍珠,从下巴悬空坠落,重重砸在沉迦宴的手背,四溅。
“哭什么。”沉迦宴把她抱去琉璃台上,抽纸给她擦眼泪,“他们伤更重,肋骨断了四根,刀——”
“。。。。。。这种事是可以比的吗?”倪亦南打断他。
不知道是在安慰她,还是在给她添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