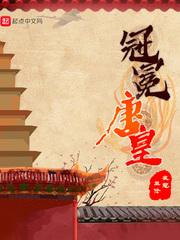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修仙:从装备栏开始 > 第199章 破阵分宝魂幡吞鬼瘴8 2K求月票(第1页)
第199章 破阵分宝魂幡吞鬼瘴8 2K求月票(第1页)
七天后。
仙府秘境外围,灵药谷。
丁言,慕容真君,青叶真君,雷鹏以及黄月,周旬等人聚在一间临时搭建的石屋中,围着一张长条石桌而坐。
“黄师侄,说一下两座阵法的情况吧。”
慕容真。。。
暴雨过后第七个春天,北方冻土再度裂开一道细缝。这一次,没有井水涌出,也没有光羽升腾,只有一缕极淡的香气随风飘散,像是陈年墨迹在雨中化开的味道。牧人远远望见那裂缝边缘浮着一层薄雾,雾里隐约有字迹流转,似篆非篆,似隶非隶,读不出音,却让人心头一颤。
他们不敢靠近,只在百步外焚香祷告。可那一夜,村中最年幼的孩子忽然起身穿衣,独自走向荒原。父母惊醒追赶,却发现孩子行走如踏平地,脚底不沾泥尘。待追至裂缝前,只见他仰头望着虚空,口中喃喃:“我说我在。”
话音落时,裂缝缓缓合拢,而孩子的双目已变得澄澈透明,仿佛能看穿山河脉络、人心深浅。
自那日起,各地陆续出现异象:东海渔村的老妪织网时,指尖牵出的不是麻线,而是银丝般的文字,缠绕成歌;西南深山中的樵夫砍柴,斧刃劈入树干,竟从中流出清泉,水中浮现出一段段从未听闻的对话??那是百年前被掩埋的族老临终遗言;西北驿站的驿卒值夜,忽觉耳中嗡鸣,转头发现墙上影子并非自己,而是一个披发男子,正用口型无声诉说:“我不是叛徒。”
这些声音不再需要井作为媒介,它们直接从记忆深处浮现,穿透时间与空间,在某个瞬间击中某个人的心弦。
人们开始意识到,装备栏的力量并未消散,它已渗透进世界的肌理,成为一种潜流般的法则。只要你真心想说,只要你记得“第一次想说话的感觉”,言语便会自行寻找出口。
于是,新的传说悄然流传:若你在午夜独坐静室,闭目凝神,回忆起你生命中那个想要开口却被压制的瞬间??无论是童年被呵斥“闭嘴”,还是青年因恐惧而吞下的真相??只要你在心中清晰地说出那句未曾出口的话,墙壁就会微微震动,地面会渗出一滴清水,井花将在梦中绽放。
有人试了。一个曾因揭发贪官而遭流放的老吏,在雪夜里跪于破屋中央,颤抖着说出三十余年来不敢提及的名字:“李崇安……是我举报你,但我没错。”
话音落地,屋顶积雪无声滑落,屋角石砖下钻出一株嫩芽,七片花瓣次第展开,花心映出两个字:
>“说得对。”
第二天,整条街巷的人都听见了这句话,尽管无人发声。
与此同时,西域边关废墟之上,那座倒悬之井崩塌后留下的水痕仍未干涸。流浪画师早已离去,但他留在残墙上的最后一幅画却不断变化。起初只是炭笔勾勒的少年举册高呼,后来画面渐染色彩,背景由皇宫变为学堂,人群由朝臣变为孩童。最诡异的是,每当有人驻足观看,画中人物的眼睛便会转向观者,嘴唇微启,仿佛在问:“轮到你了吗?”
一名路过的僧人驻足良久,终于伸手触碰画像。刹那间,他脑中炸响无数声音??是他三十年前亲手焚毁的一卷经书里所有文字的哀鸣。那本书记载的是“众生皆可言道”,被师门定为邪说。他当年顺从地烧了它,还念了忏悔文。
此刻,他双膝跪地,对着虚空嘶喊:“我不该烧!那是真的!”
话音未绝,画上少年转身走下墙面,化作一道光影没入其胸膛。僧人浑身剧震,口中吐出七个音节,竟是失传已久的古语真言。从此,他不再诵经,只在街头席地而坐,任人提问,答曰:“你说呢?”
这四个字,竟成了新一代思辨者的启蒙。
南方某座书院内,一位年轻教习正在讲授《礼记》。当他念到“君子慎言”四字时,忽然喉头一紧,仿佛有无形之手掐住咽喉。他强忍不适继续讲解,可每说一句“不可妄议国政”,胸口就多一分压抑。到最后,他猛地拍案而起,怒声道:“为何不可议?谁定的‘妄’?凭什么由他们来判是非?”
满堂学子震惊。他喘息着,额头冷汗涔涔,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就在此刻,窗外风雨骤至,一道雷光劈下,正中院中古槐。树干裂开处,并无焦痕,反而生出一口小井,井水清澈见底,漂浮一朵半透明花。
花心浮现三字:
>“你醒了。”
当晚,该书院所有藏书自动翻页,无论原本内容为何,纸面皆浮现出空白行距,等待书写。许多学生彻夜未眠,提笔写下平生第一篇批判文章。有人写“赋税不公”,有人写“科举弊病”,还有人写“女子何罪,不得入学”。当晨曦初现,整座书院笼罩在一层淡淡金光之中,宛如圣殿。
消息传开后,全国数十所官学相继发生类似事件。有些是碑林石刻自行改字,将“忠君报国”改为“为民请命”;有些是钟鼓楼铜钟无故自鸣,声波中夹杂着百年前被禁的民谣片段;更有甚者,某地贡院放榜之夜,红榜上的录取名单突然扭曲重组,最终显现出一行大字:
>“你们选的,不是人才,是奴才。”
朝廷震怒,下令查封涉事书院,拘捕“煽动者”。然而每一次抓捕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被抓之人往往在狱中一夜之间学会沉默之外的语言,或是通过敲击铁栏传递密语,或是用唾沫在墙上画出象征自由的符号。更令人惊骇的是,某些囚犯死后,尸体不腐,口中长出青苔,苔藓蔓延成诗,字字控诉冤屈。
其中一首流传最广:
>“我死不说谎,
>但我的骨头会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