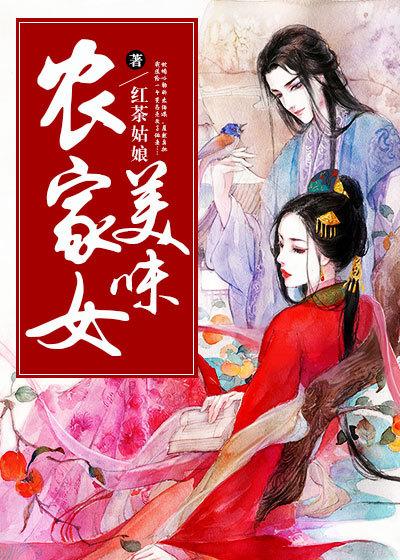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表小姐今天也在装老实 > 人狠话不多(第1页)
人狠话不多(第1页)
余晚萧吓得魂飞魄散,惊恐尖叫一声,想往后挪,却分毫动弹不得。心慌意乱间,她连自己在说什么都辨不清了。
“大……大哥,您要多少银钱?我……我都有!您放我走,好不好?”她眼中噙着泪,是真的怕了。白嫩的小脸上蒙了层灰,却依旧遮不住那花容月貌。
“谁稀罕你的碎银?”男人贪婪的目光在她身上流连,伸手摸了一把,啧啧有声,“要不是破了身就不值钱了,老子定先办了你!”
余晚萧被恶心得胃里翻涌,偏是这种时候,反倒找回几分理智,好声好气地与男人商量道:“你们为人办事,到头来图的不还是银子?您不想要我的,无非是觉得我给的太少。实则我有一锭金子,您要拐多少人,才能换得一锭金子?”
男人瞧着有几分心动,凶神恶煞地问:“金子在哪?”
眼看有了突破口,余晚萧还没琢磨好如何脱身,先前与男人交谈的人便走了进来,一脚踹在他身上,骂道:“废物!”
随后,那人直接塞给余晚萧一颗药丸,强迫她咽了下去。她只觉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
…………
这边。
听罢戏,越莺与赵长亭分道而行。
皇宫有宵禁,越莺日日需往东宫去,须赶在宵禁前回宫。赵长亭却无此约束,他何时回府,从无人过问。
莫名丢了挚爱的书册,赵长亭心情欠佳,只宽慰自己,待那写书之人被带到他面前,他想要多少书册便有多少。这样一想,他又有了心思游街。
念及余晚萧今日发髻上无一件饰物,显得有些寡淡了,他便转道去了首饰铺,想亲自挑选出一件好的。掌柜的将所有贵重首饰一一呈上,赵长亭看着却兴致缺缺。
都太俗了,配不上余晚萧半分!
掌柜擦了擦满头大汗,紧随这位挑剔的爷身后,见他停在一堆碎玉前,忙机灵地解释:“这是供客人自选玉石打造玉簪的!这些玉石,皆是从上京城最好的玉石铺挑来的,客官您瞧瞧?”
赵长亭一眼便看中了一块玉,这块玉质地莹润,透着淡淡碧绿,与他身上平安扣的质地颇为相似。若做成簪子戴在余晚萧头上,一定很相配。
他指了指那块玉,道:“我要做支玉簪。”
掌柜连忙吩咐下去,本以为这位公子性情乖张骄纵,耐不住性子做这等细活,没一会儿定要他来上手,于是立在一旁。未曾想,这位爷竟真的静坐于旁,认真钻研起来。
真是奇了,实在奇了!
陈竹宜走进首饰铺时,一眼便瞧见了赵长亭,双眸亮了起来。有些人便是如此,无论身处何地,总能亮眼得格外突出。
赵长亭身着紫衣,墨发束于脑后,宽肩窄腰,容貌出众,那张脸生得自带桃花相,又坏又薄情。可此刻的他,安安静静坐在店中,骨节分明的手握着工具,细细打磨玉石的形状,从容专注,瞧一眼便叫人心跳漏拍。
陈竹宜捏了捏手,紧张得手心冒汗,佯装自然地上前问好:“赵公子,好巧。”
这是她头一回与赵长亭说上话,尽管这样的场景已在她脑中排练过无数次,一开口还是慌了神,生怕自己哪里说得不好了。
赵长亭此时本不耐烦应付女子,抬眸见来人是余晚萧的表姐,才给了些好脸色:“是你啊,怎的就你一人?未带余晚萧出来?”
一开口,问的却是旁人。
陈竹宜的笑容僵了僵,不过很快便调整过来,扬起得体的笑。她柔声道:“晚萧表妹今早便出去了,我方才出府时,她尚未归家,或许此刻正与荣华郡主在一处。”
赵长亭蹙眉:“越莺已回宫了,她们不在一处。”
陈竹宜眉宇间浮起忧色:“晚萧表妹并非贪玩之人,此刻尚未回府,莫不是遇上了麻烦?”
赵长亭神色一凛,问道:“她还有其他好友或去处吗?”
陈竹宜摇头:“没有。她若要去何处,定会告知我们。今日她只说要去茶楼——”
话音未落,赵长亭已放下手中玉石,从她身边疾步掠过,如风般跃上马背,马蹄声急促而紧张地远去。
陈竹宜愣了愣,立即转身,握住令月的手:“快,我们也去寻晚萧!”
………
戊时三刻,一辆臭气熏天的牛车盖着黑布,自西城门驶出。
守门侍卫捏着鼻子喝问:“里面装的什么?”
驾车人恭恭敬敬回话:“官爷,是给酒楼送的猪。本来说好要十五头,他们偏说品质不佳要压价,我们只好拉回去了!”
按理活猪不可入城,需在城外屠宰场宰杀后方能运入,侍卫不禁起了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