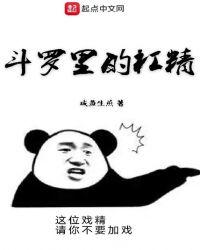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农野悍夫郎[种田] > 6070(第9页)
6070(第9页)
待拾掇好这些,天色已然擦了黑,汉子拎着编筐回去,就见山穴外的空地上,裴松正在看火,赤红的火苗映在脸上,一片暖光,见他回来,忙朗声道:“水给你烧好了,快去洗洗,我正好把面条下了。”
趁着汉子做活儿,他早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妥当,还特意换了件清爽衣衫。
就连脚上,也套了厚底布鞋,俩人成亲时的那双,只往后日子因着跑山、干农活儿鲜少再拿出来穿,而今这般板板正正的模样,倒像又成了回亲。
石灶间火声噼啪,锅中热水滚沸。
余下的小块儿咸肉用清水泡过,仔细搓洗过几遍都还泛着丝咸,裴松便提早下进锅里煮透,汤底析出浅淡的盐水,倒是连盐巴都不消再放了。
家中带来的小袋子白面,他仔细搓成了面条子,本还想着小露一手,谁想这活计比起裴椿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面条子搓细搓薄了总是断,他干脆也不管这卖相,揉擀成厚实的一条,求个福禄长寿,岁岁平安。
见他正忙,秦既白应下一声,又道了句“就来”,急匆匆进了山穴。
他手中的皮子还凝着未散的血腥气,这物件金贵,实在不敢随意搁在外面。
此时日头西沉,他先把山野鸡挪进里间安置。
这畜生的腿脚不能总绑着,要么挣扎间再勒进皮肉去,落下毛病。
好在之前已剪了它两翅的羽毛,如今飞不起来,只在洞穴里走地鸡似的咕咕唧唧。
近来它同俩人熟稔了些,心里大抵清楚,不管怎么叫骂都逃不出去,索性收起狂躁性子,安安静静地歇下了。
秦既白取了些小米子撒在地上,山野鸡滴溜着眼珠子转了一圈,随即扑腾起翅膀埋头吃起来,尖喙敲着地,笃笃作响。
待安顿好鸡,他才翻出条干净布面,把仍有些潮气的猞猁皮子仔细擦干净,里外三层包裹紧实,收进了皮货筐子里。
眼见着天色不早,汉子找了处背风的地界将木盆搬过去,脱下了衣裳。
他伤愈后身子骨越发壮实,秋凉时往水泡子里蹚也不当回事,可裴松还是给他烧好热水仔细兑温了。
他蹲过身,掬起一捧撩在膀子上,温水淌过皮肤,好生舒坦。
不由得想到今儿个长夜,脸色泛起红,趁着夜色渐浓,将亵裤也一并褪了去。
擦洗干净后,秦既白披下头发,只用条绦带随意系上,几缕长发散在身前,虽仍有些毛糙,却掩不住清俊温然。
他出来时,面条已经出锅,裴松正在炒兔肉。
上回家中吃兔子,汉子身伤未愈,裴椿都不敢放红辣,就着青椒段炒香,眼下没了顾及,明儿个也该起程,裴松便将余下的红辣椒都放了,热气腾腾的一锅子,呛得人眼泪四溢,却也口水横流。
见人在石凳上坐定,裴松将面条端到了他跟前:“山野条件不比家里,就一个锅子好烧,你先吃着,别坨了。”
秦既白垂眸瞧着这一碗咸肉面,热气徐徐升腾,和着石灶间浓郁的辣味齐齐往眼底钻,闹得人红了眼。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给他庆生辰了,阿娘过身后,他的生辰只与天地山水作伴。
他躺在坡子上,层云千叠,一根毛草叼进嘴里,嚼不出咸淡。
裴松见他不动筷,知晓他是在等自己,这小子向来犟,他没再劝,翻炒间被红辣呛得咳嗽:“马上、马上就好。”
“嗯。”秦既白轻轻应下一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里极尽温柔缱绻,石凳太矮,他手肘抵在膝头,又撑起下颌,“松哥,你今天喝酒吗?”
打着锅壁的铲子顿了下,裴松扭身看他,正见汉子一双眸子灼热而坦荡。
他伸手挠了把泛红的耳朵:“你晓得的,哥不大会喝酒,到时候再闹你。”
“那喝吗?”汉子又哑声问了句。
裴松咽了口唾沫,就感觉胸膛子似是燎起一团火:“那……那喝吧。”
黄酒坛子落上石桌,汉子轻轻启了封,给俩人各倒了小半碗。
酒液清泠泠地淌进碗底,一股子甘洌的辛香。
白面不多,只堪堪做了这一碗长寿面,裴松给自己蒸了个干面饼子。
一袋子干面馍饼,对付了半个来月,可算要到头了。
秦既白却执起筷子,照着那白面条中间夹去。
“这是长寿面,不能断。”裴松急着拉他手,“从头吃到尾,长命百岁。”
秦既白余光扫了眼他冷碗里的饼子,背进山这么久,面饼受潮发过霉,裴松心疼粮食,剥掉了霉处继续吃,却用这金贵白面给自己新做了一碗,他沉声道:“我不讲究这个。”
裴松歪头瞧着他笑,现下倒说不讲究这个了,没成亲那会儿,是谁因为个生辰八字哭丧个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