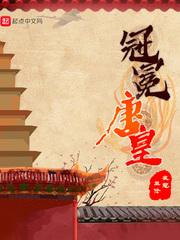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嫁错 > 7076(第7页)
7076(第7页)
说罢,转头看向一众官吏,心平气和地吩咐把现有案宗呈递上来,并传刑部尚书亲自过来,从头再审。
······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此前虽已有人签了贿赂卫国公夫人的认罪书,这会儿又纷纷翻供,言是被刑讯逼供迫不得已才签的,实则无意贿赂,只是想表谢意。
但涉案人员众多,且涉案官吏虽然品阶都不高,却几乎遍布各个衙署官司,六部九寺五监,虽都是底层名不见经传的小吏,还是令齐帝吃了一惊。
“你们……求学之时都受过姜氏的恩惠?”圣上若有所思地看着一众小吏。
众人都道是。
圣上又看向姜姮,暗暗盘算。
她在还未嫁给顾峪时就已开始这桩事,且看时间,早年相助之人要多得多,嫁给顾峪后,反而比之前少了许多,若说她是在为顾峪笼络人心,又实在不像。
秦王亦看出圣上疑虑思量,对姜姮问道:“你如何认得这些士子,又为何决定帮助他们?”
姜姮早年相助之人,多多少少都与燕回有些关系,后来相助之人,则是在寻燕回时遇上的有缘人。但这些因由,如何说得出口?
可若没有正当的理由,怕在圣上眼中,就是结党营私居心叵测了。
要如实说么,如实说了,顾峪的面子往哪放?
姜姮却也不敢说谎,尤其此时,她编不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既能不提往事保全顾峪面子,又足够正当能打消圣上猜疑。
“我知道为何。”顾峪忽然开口。
圣上和秦王都看向他,他却没有继续说,道:“这件事,我只跟陛下你说。”
秦王皱眉。
圣上想了想,依言屏退所有人,连姜姮都遣了出去,只留下顾峪。
“我夫人有位远房表兄,从前在国子监读书,但家境贫寒,一直是我夫人在予他钱财,其他士子都和那位远房表兄交好,是那位远房表兄央求我夫人帮助那些人,陛下若不信,可去问问那些小吏,认不认得一个叫燕回的人。”
顾峪虽称为远房表兄,但圣上怎可能听不出来其中弯绕?
一个关系淡漠的远房表兄,如何能叫女郎死心塌地地私与钱财,还爱屋及乌地帮了与他交好之人?
“她那位远房表兄,现在何处?”圣上追问了句。
“死了,四年前就病死了。”顾峪道。
圣上意味深长地“哦”了声,亦终于明白姜姮为何对此事闭口不言。
“陛下,”顾峪神色依旧冷厉,叫人分不清他到底是在恼怒当下之事,还是因为思及妻子与那位远房表兄的旧事心生不悦。
“姜氏没有那个胆子结党营私。”
说罢,停顿一息,并不袒护那些涉事的官吏士子,直言道:“那新科状元,和其他一众小吏,或许不单单是感激我夫人,当是有心讨好结交,但我夫人必定没有此意,她若想到这层,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去赴约。”
圣上什么风浪没有见过,虽然惊讶于姜姮的“广结善缘”,却还不至于因此就草木皆兵,认为女郎有心谋逆。
“你觉得,如何处置妥当?”圣上没有表态信与不信,左右事情至此,从现有证据看,也的确定不了姜姮和那一众官吏士子的罪,但是,若丝毫不做警戒,放任自流,却也不能。
圣上素有仁义宽厚之名,不能无缘无故惩戒何人,更何况那人是顾峪家眷,而顾峪又刚刚大功还朝,他不想背上一个打压功臣、小肚鸡肠的名声。
这件事就看顾峪怎么解决。
“恒生会既已成立,那一众小吏有心帮助其他寒苦士子,臣以为,不必解散。”
“哦?”齐帝笑呵呵地,叫人看不出半点同意与否的虚实。
“恒生会既是为帮助寒苦士子而设,自当归于国子监管理,若能沿为定制,为寒苦士子做一盏保驾护航的明灯,众士子定会感念陛下爱民惜才之心。”
“陛下有意改制科举,促其公平公正,恒生会在此时成立,也可谓水到渠成应运而生,便权做改制先导。”
齐帝不辨虚实的笑容中,此刻总算透出些明显的嘉许之色。
“顾卿心系天下,实为社稷之幸。”
顾峪却知这番夸奖的分量,又道:“不管臣的夫人当初助人是因何而起,臣愿意继续发扬此举,向恒生会捐送白银万两,光大其力。”
齐帝哈哈大笑,“顾卿才思敏捷,此计甚好,就依你之言,朕会遣一妥当之人接手恒生会,如你所言,助学济贫。”
想了想,继续含笑说道:“往届的状元若能有顾卿的胸怀,光大恒生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