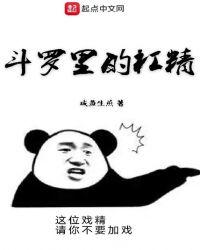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被迫委身疯批皇子后 > 6070(第7页)
6070(第7页)
旁人不认得这个稀罕物,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便是落雁峡设伏当日,韩因身上亲自挂着的令牌。又或许,那时候,他以为的韩因就不是韩因,而是伪装成韩因的许银翘。
想到许银翘,裴彧心中不自觉又嗤了一声。
墨玉上本来刻有印痕,上面写的是西北军中的番号和队列。现在,字印被刻意磨去,只留下浅浅的凹坑,原本品相上佳的一块清透玉石,被斑驳的痕迹,映衬得分外粗糙模糊。
裴彧的手指摩挲着玉石上的凹坑。
他从墨玉模糊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脸。
他此时的表情一定很期待,裴彧心想。
他们煞费苦心逃到这里,抹去一切存在过的痕迹,但还是留下了这样一条线索。
说明什么?
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了。
裴彧一想到这点,连日阴郁的心情,竟不自觉出现了欣喜的光芒点点。
但这种欣喜只维持了一瞬间,他就回过神来。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找到韩因,然后将许银翘的尸体带回来。
老板娘低头看着地面。
暗色织金下摆在她面前划过,如此上乘的面料,穿着它的人一定是一样大人物。
那个拿玉石远道而来的男人,与面前这位大人物,会有什么关系呢?
小官从旁正要发声,有人制止了他。
上头男人的声音响起:“我亲自来审。”
*
“这里,便是他们住过的房间了。”
老板娘打开木扇,露出里头清洁窄小的居室。
裴彧走进来,后面的人簇拥着,很快就把老板娘挤到了最后头。
“这里只有一张床?”裴彧的声音带着些冷意。
没人回答。
裴彧回过头看,带路的老板娘不知道被挤到了哪里。他的面色更加不好看了,伸出两指,朝旁轻轻挥了挥,身后侍从自觉地格挡开闲杂人等,空出一条路,让老板娘直通人群的最前端。
“啊、是,是。”老板娘愣了一下,有人握着她的肩轻轻一推,她一个踉跄,走上前去。
“那男人是一个人来的?”裴彧眯起眼睛。凤眸微狭,让他看起来像一只狐狸。
“似乎不是……”老板娘翻着眼睛回忆,“和他一道的,还有一只脏兮兮的矮马,和一辆板车。你说奇怪不奇怪,人不骑马,倒用马拉板车,我当时看到他,就觉得这人有点愣,谁知道他一出手那么阔绰……”
一想到此前经受的牢狱之苦,老板娘在心里打定主意,下次再遇到这种飞来横财,得先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够接得住。
“那板车上,可放着什么物件?”裴彧问。
“物件嘛,倒看不清。”老板娘手舞足蹈地比划,“上头铺了那么大一样毛毡子,里头鼓起一条,看模样,也不知道是不是个人。噢,不过毡底露出一角,倒叫我瞧明白,底下藏了把刀。带血的,可吓煞人。”
说刀那把带血的砍刀,老板娘此时还心有余悸。
裴彧的眸中深色更浓:“这么说,那板车上,就是入住之人最重要的物件了。”
“是也是也。”老板娘不住点头,“那人特地要了这么一间大屋子,就是把板车放在室内。我们店家要帮他推,他还不让,非得亲自来运。”
裴彧心底有个声音不住重复:是了,就是这里了。
但一股怯意浮上他的心头。
近乡情怯。
裴彧第一次体味到这四个字的味道。
离许银翘的尸体越近,一个事实就越无可避免。
许银翘已经死了。她躺在板车上,被韩因悉心照料。她什么都感觉不到。
生前的喜怒哀乐,悲伤与愤怒,都离她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