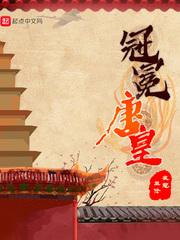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黑与红 > 05(第1页)
05(第1页)
05
此时,工作面响起沉闷的叭叭声,田宝琪赶紧和韩正群撤到了回风巷,溪总、肖总、田队长立即把矿灯对准工作面,马班长也从后边跑了过来,一起观察工作面的动向。
一切又很平静,只是响了一声再没有什么动静。仔细观察每根柱子已经吃上了劲儿,新打的木垫柱,贴顶板的地方又被压开了花……
田队长和马班长这两位老采煤,凭以往的经验,觉得这是老顶来压的前期预兆,搞不好要推顶。马班长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应该赶快回收,推顶就麻烦大了。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收尾成功的曙光就在眼前。谁知顶板又要来压,也许是在故意出难题,考验这帮和大自然争时间抢速度的勇士们。
马班长还是和上次一样,一马当先在最前面,他先用锤将柱子轻轻敲了一下,发出同样清脆的反弹声音,力都在柱子上了,锤举起来两次都放下了,最后还是退了出来。关键时刻马班长心里清楚,肖总一直在掘进区干,采煤实践经验欠缺,这个肖总他自个儿知道,不如田队长,溪总在大学是学地质的,这样的场面他听都没听说过,谈不上现场指挥,现在只好看田队长咋样处置了,在这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指挥员说不到点子上,就是瞎指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马班长叫田宝琪和韩正群这两个他认为配合默契的老采二队的人跟在他后面,自己爬进去了,看来真是到了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时刻了。田队长在巷道和工作面的三岔口密切观察顶板动向。一切都按照程序进行,谁也没有勇气说一句话,只是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推着自己,无论前面是刀山是火海,都无所顾忌,不管一切地往前冲,向未知争取时间。马班长对着靠老空吃劲儿的那根柱锁,咚的一锤过去,只听见哗啦一声,瞬间,石头噼里啪啦地推倒未回收的工作面,巨大的冲击力推倒了回风巷的支护。顶板塌下来的强大气流裹起煤尘,如同八级地震,将每个人头上的安全帽冲出好远,整个巷道里什么也看不见,根本不知道谁在啥位置。只听见肖伟光沙哑的哭喊声,坏了,快救人啊!快救人,我吓得大声叫喊,双腿已经瘫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过了约一分钟,溪总才反应过来:人咋样?人咋样?赶快打电话告诉调度室,出事故了,让医院火速下来抢救,千万、千万……韩正群最先跑出来了,脸色铁青,目光迟钝,哭丧着说,快、快,马班长、田班长在里面!肖伟光问:田队长哪里去了?正群说:没见、没见队长,快救班长啊!
待煤尘过后,像篮球场大的工作面冒落的有几十米高,龇牙咧嘴的碎石还不断地往下掉,从冒落的石头中看到有矿灯光。韩正群喊道:就在那位置,班长和副班长在一起!我扯碎着嗓子叫唤马班长、田宝琪,没有任何反应,只听见靠煤壁一侧有微弱的呻吟。王金钟说:对,田队长就在那里,他跟我和永安招呼顶板的。金钟来矿前在当地的小煤窑干过,入矿培训后田队长看好他有井下工作经历,找劳资科要求给分配到采五队的。
肖伟光环视四周,看到靠巷道煤壁的顶板比较稳定,果断地说:赶紧从煤壁把石头搬开救田队长。煤壁有柱子支撑,石头下来形成夹角,很快打通了通道,把田队长拉了出来。田队长头上有两个伤口,不停地流血,人已经昏迷不醒,被赶来的医护人员接走了。
矿长刘东春、书记李高明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知道还有两个人在里边时,狠狠地将溪石彬骂了一顿。这时候肖伟光已经指挥我从救田队长的地方向马班长的方向刨开了一道洞,我看见马班长趴在田宝琪身上,有三块楼板大的石头压在他身上,矿灯甩出去有两米多远。我爬到距离班长不到一米的地方时,被压碎了的木柱挡住无法接近,只好让韩正群给我拿锨将柱子边上的浮煤挖下去,上面有那根木柱支撑着,然后用升柱器一点一点地把压在他俩身上的石头顶起来。先把田宝琪拉出来,我手搭在他嘴上摸,还有气,而马班长一只手搭在田宝琪的背上,一只手还紧紧地攥着锤,嘴里出的血把田宝琪的上衣染成了红色。营救前后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我刚刚把马班长拉出来不到一分钟,哗啦一下,顶板又二次来压,摧毁了整个工作面。
这次工作面回收以血的代价画上了句号,非常沉重的句号。马班长这盏传奇又富有争议的油灯灭了,就这样悲壮地走了,走得和他的性格一样的干脆、壮烈,走完了他实际年龄六十一岁的人生历程。尊敬他和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都发出同情之心,我们哭得都哭不出来眼泪了。他的妻子井秋香和他娘家兄弟被矿上的车接来处理后事。井秋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妇女,瘦小的个子,还稍带驼背,灰暗皮肤,长年累积的生活风霜在她脸上留下深刻的痕迹,透过那双有神的眼睛,能看出经历人生磨砺后的坚强。她话本来就不多,也不会说,在天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头上时,只有一串串绝望的眼泪。
矿上安排李巧凤和另外一位老乡矿工家属陪着井秋香,后事全权由她弟井军胜处理。姐弟俩没有任何非分的要求,一切按照矿上的标准赔付,两天时间就谈妥了。行政科钉了一口松木棺材,我们下午到煤场给矿上安排拉人的解放牌卡车装了半车煤,然后到矿医院太平间装棺材。在太平间给马班长穿衣服入殓是李巧凤一手操办,没有让井秋香见人,按照老家当地的风俗,人死了陪葬一只大红公鸡镇魂,还不许还价,表示对逝者的尊重。必须满足这个要求,队上安排专人在当地高价买了一只红公鸡作为陪葬品。车下午八点准时在渭北矿务局医院太平间入殓,傍晚悄然离开,三百公里的山路走一个晚上,正好赶上天麻麻亮下葬。
矿上只安排一名工会干部和区队侯文江书记、掘三队副队长刘新民送行。为什么要派刘新民副队长呢?刘新民和马班长是一起招工来的乡党,他俩没有在一个队,井下三班倒,都各忙各的事情,再加上两个人根本不是一路人,虽是乡党,来往还不如旁人。矿上担心怕下葬之后村上人挡住车不让走,决定让刘新民这个当地人去,而且新民还是干部,遇到意外情况肯定要向着组织。矿上每年死亡事故都在三起以上,因后事处理不好,埋人后扣车、扣人的事情屡见不鲜。工会主席王光银还专门找刘新民谈话说,你是中层干部,把车扣了,还是砸了,看你回来咋向矿上交代,副队长就别干了。刘副队长当面保证:请主席放心,我们家乡地域偏僻、穷,但人老实,民风淳朴,不会有啥事。
我一再请求送马班长回家,侯文江书记终于同意了,按照请假对待,纯属个人行为,不代表区队。只要能去就行,协议工本来就没有资格代表组织,也没敢往那上面想啊。
在矿务局太平间诀别时的情景非常感人。矿上在半保密的情况下,叫了采五队六个给汽车装煤的小伙子到太平间装棺材上车,不知道是谁泄露了消息,原采二队和马班长的老乡共有二百多人赶到地点为马班长送行,把那简陋的太平间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夕阳照耀下的三伏天,天气死沉沉的闷热,院墙边那一排参天白杨树的叶子一动不动地耷拉着。空气中没有一丝微风,人都烤得汗流浃背。本来就被伤感、痛惜、凄苦、哀恸笼罩着的气氛,加上这么多人为马班长送行的悲壮场面,简直令人窒息。矿上看到这种场景,调来了十几个公安维护秩序,防止出现过激行为。
李巧凤和几个老乡家属在给马班长整理衣服,李巧凤的女儿郭春娥也来了,她挤在母亲的身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给母亲当下手。当行政科木工将棺材盖好,封钉时,郭春娥扑在棺材上哇地放声大哭,在场不少人流下了眼泪。李巧凤抚摩着女儿的背,紧抿的双唇颤抖着,自己脸上也滚下两行长长的泪。封棺的木工师傅看来也熟悉马班长,泪流满面地说,寡子,你走好,你走了解脱了,可是,留下后面这一摊子咋过活呀。这位师傅当然说的是眼前哭成泪人的郭春娥娘儿俩了。
棺材是在夜幕降临时装上了煤车,送行的人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医院,因为来的人几乎都是下井的矿工,要赶回去上下午班或者夜班。穷苦人家,就靠下井挖煤养家糊口,一个班也耽搁不起啊!矿工会生活部长高拥琦、书记侯文江、副队长刘新民回矿接井秋香坐小车提前两个小时走,到村上安排人卸车,小舅子井军胜和我坐装棺材的车,得等到十点过后,夜深人静时出医院、过县城,赶天亮到墓地下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尤其是西部相对偏僻落后的地方,人们坐车能见到柏油马路都是稀罕,这段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全穿越在山川和沟壑地带,都是石子路,坑坑洼洼,非常难走,好在是国道,路面比较宽,夜间开上半小时也见不到一辆车,行程还比较顺利。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翻过一个一个叫不上名字,也没有路标的山梁,车行驶到一个叫分水岭的地方,下去就是马班长家县城的地界,解放牌汽车突然失控,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车头折回到来路的方向。
我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下车拿手电筒照,好险啊,如果弯子再转大半米,车就掉到深不见底的沟里了。好在棺材一半在煤里,工人又用小孩胳膊粗的麻绳前后死死地捆着,才没有滑落下去,意外的是放在棺材前头的那只大红公鸡,一路都没有吭声,这下被惊得咯咯叫个不停,三更半夜,在这荒无人烟的山里,凄怆和恐惧像雾一样越发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