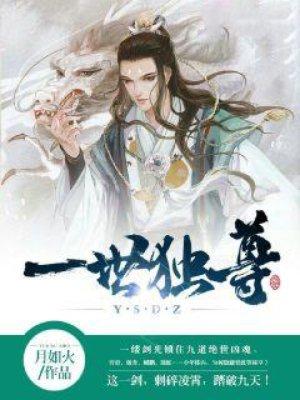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万灵女汉子 > 第二十七章 风流将军的人生体味(第4页)
第二十七章 风流将军的人生体味(第4页)
**,正躺着那位绝色歌女。衣裤已经褪去,玉体横阵,泪眼婆娑令人心动。
赵中玉见女子嘤嘤哭泣。问道:“你哭啥?”
女子哽塞道:“老爷,小女子卖艺不卖身,可恨那郑稷之,把我强抓去献给杨军长玩弄。杨军长一天一换,夜夜尝鲜,今晚,他们又强逼我来……伺候老爷。”
赵中玉呆住了,半晌,便说道:“去吧,你也是个苦人儿,我……不难为你。”
女子陡地坐起身,痴望着赵中玉,分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赵中玉喝道:“快走吧!”
女子吓得跳下床,慌不迭地跑出房门。她窜下楼梯,刚跑进厅堂,就被两名幺师抓住了。
女子凄惶喊道:“不怪我!不怪我,是老爷撵我走的!”
一幺师对同伙说道:“你留在这里,我把她带回去。”恶狠狠把女子推出门,“走,回去再听候县长发落。”
赵中玉听见楼下声响,早已出屋掩在楼口暗处,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冷笑一声,重新回到房里,然后推开了窗户。
他的目光掠过鳞鳞黑瓦,飞到了远处县衙方向。他好像看到县衙深处的一间厢房的窗户上,仍透着淡淡的微光。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筱竺那张美丽而清秀的脸蛋……自从大辟之日,自己亲眼目睹了筱竺在城楼上的嘶声呼喊,后来又秘密与筱竺幽会后,赵中玉才知道筱竺的命有多苦,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筱竺对自己的感情有多深。而作为本应对筱竺的一生苦乐负有责任的男人,自己不仅无能为力,反而怨恨筱竺的不贞是多么的荒唐无理。那种长时间萦绕在心中的憎恶之情,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充塞心中的,是对筱竺的同情与怜爱。他已经再也忘不掉筱竺那双眼睛,那么悲怜,那么凄切……
他“扑”地吹熄了烛火。
小巷清冷,赵中玉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兴隆客栈,独自来到了县衙后墙外。
他一跃纵上墙头,穿过绿竹扶疏的庭院,来到厢房门前,见四下无动静,遂轻声叫道:“筱竺,筱竺。”
屋里响起了细碎的声响,稍顷,门开了,赵中玉一闪而入。
门,立即关上了。
一个人影从竹林中悄无声息地钻出来,蹑行至窗外竖耳偷听。
黯淡的天光照着他那张阴狠的脸———那是荣昌县警备队长胡之刚。
墙上的挂钟早已敲过了十点,郑稷之倚靠在雕花大牙**,一支接一支抽烟,依旧毫无一点睡意。赵中玉一进荣昌县城,住在赵家老宅里的郑稷之便乱了手脚。双方尚未正式交锋,赵中玉已经赢了第一个回合。郑稷之万万想不到手握数万重兵的大军头杨森,竟然会对一帮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残匪迁就让步,这不仅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威信,而且赵中玉与他同处一城,仅相隔两条街巷,更让他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为防不测,郑稷之已下令从警备队调了百十号人到县衙,将他所住的内院铁桶般围了起来。即便如此,他仍放心不下,又让胡之刚住进内院,作了他的贴身保镖。如此防范赵中玉与他那十来个手下,可以说是确保无虞了。但他也明白,这么做,很有可能是聊以**罢了。他真正担心的,是赵中玉为报灭门之仇,把交出他郑稷之也作为一个释放西票的条件。果真那样,他就是大祸临头了———他非常清楚,在他与外国人质之间选择,杨森是决不会吝啬一个中国人性命的。
杨森来到荣昌后,作为一县执政,他曾两次前去谒见,都吃了闭门羹。过后,他才旁敲侧击地从李江副官长口中了解到杨森在与外国使节密谈。密谈什么?不言自明。久经宦海的郑稷之立即断定杨森欲借此次前来挽救西票的机会,与外国列强搞交易,求得列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再挥师西上,剪除刘湘,重据省城成都乃至整个富饶的川西坝子,以报前次兵败之仇。那么,交易若不成,他定然会令部下猛攻老鹞岭、万灵寺,强逼土匪杀死西票。而交易若成,他则会痛痛快快地答应土匪提出的所有条件,甚至包括交出他郑稷之的脑袋!
唉,当初未能斩草除根,留下赵中玉这个魔鬼,真是最大的失误哟!
他在一旁长吁短叹,动来动去,把罗芸花也给搅扰醒了。
罗芸花狠狠地盯了郑稷之一眼,耷着眼皮说道:“都啥时候了,还不睡,床头柜上不是有你买的安眠药么。”
郑稷之忧心忡忡地应道:“赵中玉大模大样地住在城里,眼下连杨森这样的大军头也让着他几分,我怎么睡得着……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罗芸花嘴一撇:“他来,不就是冲着傅筱竺么!把那小贱人送还给他,不就清静了。”
郑稷之瞪她一眼:“真是妇人之见,赵中玉此行,可不是单为了傅筱竺啊,他是冲着我郑府一家老小,包括你的脑壳来的。”
“啊,我的妈呀!”罗芸花顿时睡意全无,翻身坐起,“稷之,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不正在想主意么!”
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紧闭着嘴巴,让那烟雾一缕缕从鼻孔中慢慢悠悠飘逸出来。
半晌,他忽地一扭头,对罗芸花说道:“只能像眼下这样了,对傅筱竺明松暗紧,拿她勾住赵中玉的魂儿……哼,真到了要命的关头,这小贱人说不准还是我手中的一张王牌哩。”
“嘭嘭!”门上响了两声,紧跟着有人低声叫道:“县长,县长。”
郑稷之听出是胡之刚的声音,赶紧披衣下床,将门打开。
“县长,赵中玉又钻到二姨太房里去了。”
郑稷之阴沉着脸:“果不出我所料。”沉思片刻,决然道,“你继续前去监视,万万不可惊动他。我马上去见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