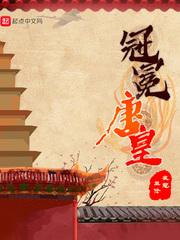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三个火枪手(全两册) > 第四十七章 四个伙伴的密谈(第7页)
第四十七章 四个伙伴的密谈(第7页)
紧接着是第二阵枪声,三颗枪子儿射穿了餐巾,真的使它变成了一面军旗[3]。营地那边喊声不绝,大家都在喊:
“下来,下来!”
阿托斯下来了;三个伙伴一直悬着颗心在等他,这会儿见他乐呵呵地出来了。
“走吧,阿托斯,走吧,”达德尼昂说,“快,咱们得快;现在我们除了钱什么也不缺了,再让人打死就太冤了。”
可是不管同伴们怎么说,阿托斯依然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他们眼看劝也没用,就跟着他放慢了脚步。
格里莫挎着他那个篮筐一直在头里走着,这会儿已经走到了敌军的射程之外。
不一会儿,只听见后面枪声大作。
“怎么回事?”波尔多斯问,“他们在朝谁开枪?我只听见枪子儿呼呼的飞,可没看见有人。”
“他们在朝那几个死人开枪。”阿托斯回答他说。
“那几个死人是不会还击的呀。”
“正是;所以他们就会以为有埋伏,就会商量对策,就会派人上去谈判,等到发现这是在跟他们开玩笑,他们的枪子儿已经追不上我们啰。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跑得浑身是汗,落下个胸膜炎什么的。”
“噢!这下子我明白了。”波尔多斯惊叹地嚷道。
“这真让人高兴!”阿托斯耸耸肩膀说。
营地那边的法国兵看到四个伙伴正在不慌不忙地往回走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临末了又响起一排枪声,这回枪子儿打得四个伙伴身旁的砾石乱蹦,耳边尽是尖利的飕飕声。拉罗谢尔那帮人总算把棱堡夺回去了。
“这些人可真是笨手笨脚的,”阿托斯说,“我们一共打死了多少?十二个?”
“十五个吧。”
“压死多少?”
“有八九个。”
“而我们这边连一个受轻伤的都没有?啊!不对!您手上怎么啦,达德尼昂?好像有血?”
“没事。”达德尼昂说。
“一颗流弹?”
“不是。”
“那究竟怎么啦?”
我们前面说过,阿托斯爱达德尼昂有如爱自己的儿子,这个性情刚毅沉郁的火枪手,有时会对这年轻人表现出一种父爱般的关切。
“擦破了点皮,”达德尼昂说,“推墙那会儿,我的手指夹在石块和戒指的钻石当中,皮给擦破了。”
“这就是有钻石的好处,我的少爷。”阿托斯口气有些不屑地说。
“嗨,”波尔多斯嚷道,“原来有颗钻石在这儿,那可真见鬼,既然有钻石,咱们还要哭什么穷呀?”
“可不是吗!”阿拉密斯说。
“太棒啦,波尔多斯;这主意出得不赖。”
“那还用说,”波尔多斯受了阿托斯的表扬,变得神气活现起来,“既然有钻石,就把它卖了吧。”
“不过,”达德尼昂说,“这可是王后的钻石呀。”
“那就更有理由了,”阿托斯说,“王后救她的情人白金汉先生,那是天经地义;而我们是她的朋友,王后救我们也合情合理:我们还是把钻石卖掉吧。神甫先生意下如何?波尔多斯就不用问了,他已经表了态。”
“我认为,”阿拉密斯红着脸说道,“达德尼昂的戒指不是情妇给的,所以并不是定情的信物,把它卖了也未尝不可。”
“亲爱的,您说起话来可真像个神学家。总之您的意思是……”
“卖掉这颗钻石。”阿拉密斯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