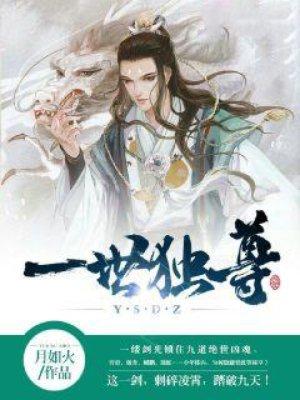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穿成阿甄那些年[三国] > 马球倒v第一更(第2页)
马球倒v第一更(第2页)
后边的如陵听了都嫌酸,忍不住对自家堂兄翻白眼。
可这话却实实在在砸进了袁尚的心窝,嘴角压不住笑意。
“是,空恼旁人作甚,我只念着今日的好彩头!”说罢,他便骑马奔到了双球门下。
与此同时,还不清楚发生什么的季蘅随袁熙落了座。婢仆刚沏上茶水,甄尧几个就凑过来问安了。
“终于把您这大忙人盼来了,原是娶了新妇,便将咱们弟兄忘了个彻底干净?”
袁熙不由含蓄地笑笑,还没等他开口,魏讽先回答焦触那话:“诶,这倒怪不着旁人,忘了你又如何?谁叫你就长着副波澜不惊的阔面,猛扎进那人堆里,宛如江入大海,分不清楚,都是水啊!”
今日各自为战,列位的火药味也浓了些。
焦触不服输地回道:“怕你上辈子是块鹅卵石子,遭人踩得太多,这辈子托胎,令尊才赐给小儿了这么个名字和毁天毁地的破嘴!”
“莫逞口舌之快,”谢容允明里劝架,暗里却在拱火,“管它什么色儿,不若马球赛上定真章。”
他们半分玩笑半分认真地吵吵闹闹,险些挽起袖子互擦口水了。
一旁的季蘅却显得颇为无聊。今日的马球赛于她而言,没什么好看的,自己既无法上场,打马球的人里还有她极讨厌的。
四种颜色混在一起很杂乱,明晃晃透着“离心”二字,果实还未成熟,既得利益者们就开始积极瓜分了。
这时,甄尧悄然走到了妹妹身边,并从袖子里滚出一颗山李,装作不经意地丢了过去。
忽就想起小时候,兄妹俩经常在严肃正式的宴席上偷尝零嘴,全然不顾大人们平素里的教诫,那是专属孩子的秘密行动。
季蘅喜食酸李,她微抬眼,斜瞥了甄尧一下,似笑非笑的,分明是在埋怨哥哥小气给少了。可再转眸,却又晦气地碰上了谢容允那莫名冷峻的目光。
凑巧对视的片刻,便似细针猛地扎进太阳穴,一阵短暂又不可言喻的疼感倏尔袭来。
谢容允一定也感同身受,只是他表现得更麻木,没有直接移开目光,反而放在了季蘅胸前的那支鱼戏莲璎珞上,盯了片刻,不知想起了什么,又面不改色地继续说:“二公子,您今日不如也赏个脸,陪他们打打马球?”
“不对啊谢兄,这难道也是你的场子?怎么都开始替尚弟揽活了?”
谢容允这才重新看向袁熙,诙笑着摇头:“园子场子的,我倒还够不着那本事,不过,今日的彩头,确是我等亲自打武威郡运来的。”
“是什么?”众人皆好奇。
“一尊三足腾空却仍屹立不倒的铜奔马。”
“三足腾空?”
“千真万确,精妙绝伦。公子还请细看。”
原本季蘅是不太感兴趣的,可越听谢容允的描述,越觉得似曾相识。
于是乎,她也抬眼望去,隔壁矮案上摆着的——
老天爷啊,这不活脱脱的……真的好像那个甘肃省博物馆里著名的“马踏飞燕”!
袁熙见自家夫人似乎很感兴趣,便要领她走近了些观量。
而季蘅正满心嘀咕呢,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的插图,如今穿越千年,竟崭新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了。
这回,可不是在看死气沉沉的摆件,她看的是闪闪发光的历史。
“确实巧夺天工。”
季蘅左右打量,十分认真,绕到侧边看时,正对着马首,只见它栩栩如生地歪着脑袋,表情狰狞;滑稽归滑稽,也符合奔跑时的状态,不得不赞叹老祖宗的智慧,但多看几眼,她最后还是没忍住笑出声。
闻此,袁熙便问:“喜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