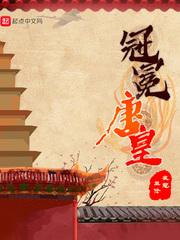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涉野与逐光 > 第 33 章(第2页)
第 33 章(第2页)
一来二去,她连蜜饯和点心都吃腻了,每天回去最大的事就是想尽办法逃避喝药。
一开始她会打发丹烟去办事,偷偷从窗户倒出去,但没几天就暴露了,最后被敖敦和丹烟两个人紧紧盯住喝药。
半个多月过去,药庭焕然一新。
试种田在学徒们的精心呵护下,越来越多的南药幼苗顽强地探出了头,积雪也没法拦住它们。不少以工抵钱的牧民们主动换着班在药田边劳作,如果是孩子或少年少女,就在暖室递工具、端药,帮忙照顾病人。
前厅药柜里,来自南方的药材与北地新采集的草药并列存放,被陆元君管理得仔仔细细。
药庭每日按宣卿开业那天提出的制度运作,虽不能致富,却也足够维持自给自足,甚至还能略有结余,被用来体贴公主的陪嫁,偶尔为药庭添置些新的用具。
冬天还没过去,冷就不说了,草原上全是雪和冰,只有那日都他们那种久在马上的人才能继续去奔狼原玩,宣卿去不了,只能一边祈祷着春天快些来,一边把心血都投入药庭。
她不会诊病,从前想跟着太医学,却总是不得要领,最后只好承认自己没这个天赋,以至于到现在连个脉都不会摸。
不过钱都是她出的,也不必非要出力了。索性就每天跑来做做监工,查查账本,再教教孩子们认字写字,她也有想过在苏日图州办几个学堂,但目前实在是没空,计划还没个雏形呢,总得分好先后顺序。
敖敦变狡猾了是真的,总是以路上有冰、她太劳累骑马不专心不安全的理由要求她和自己同乘一匹马。
“南盛的年节是不是要到了?”敖敦在她身后冷不丁问出这么一句。
宣卿靠着他打了个哈欠,眨着眼想了一会儿,“还真是,马上月底了。”
她语气有点慵懒,也有些失落。因为南盛在整个一月里都会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但北陆人信奉长生天,只会跑到神山脚下或者宗教之地去祭拜进贡,城里一切照旧,结果她又忙,就彻底把自己故国的节日给忘了。
从前过年,母后都会亲手为她缝制新衣,一起剪漂亮的窗花贴在她宫里的窗户上,就连一向忙碌的父皇也会腾出时间来检查她和哥哥的功课,宫里大大小小的妃嫔皇子坐在一起吃饭,每个孩子都能收到属于自己的礼物。
父母走后第一次过年,她和宣霁沉默着坐在圆桌边,妃嫔们有说有笑,小心翼翼地试图带动他们,但没起作用。
第二年的春节是和青驹在青州过的,还有那两个雪里挖出来的可怜乞丐兄妹,挤在一个小客栈里,面前炖了锅热乎乎的汤,青驹挽剑花点了烟火,还稍微有点意思。
不知道青驹现在是不是和皇帝哥哥一起过年呢,宣卿抬头向南边看了看。
敖敦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接下来的两日他似乎更忙了些,傍晚来接她会稍晚片刻,身上偶尔会沾染一点淡淡的、不属于王庭惯用的香料气味。
一直到一月二十八号,也就是南盛的除夕。
宣卿像往常一样忙到天色渐黑,靠在门边等了一会儿,却没看到敖敦的身影,不过桑伦珠倒是提着个红色的包袱冲进来。
“敖敦没空来接我?”宣卿有点丧丧地问。
“不不不,”桑伦珠一把拉了她往后院的大暖室去,“嫂嫂真是的,连我哥在哪儿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宣卿诧异着被拉进后院,发现那暖室里传出交谈的声音,还隐约有人影晃动。
桑伦珠得意洋洋地回头:“嫂嫂就等着吃惊吧!”
当她走到后院中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平日里用来堆放药材和安置病人的暖室,此刻竟被人精心布置过,檐下挂了纸糊的大红灯笼,与北陆建筑的风格大相径庭,但里面的烛火又那么明亮温暖,不像冷冰冰的宫殿。
她一直在前面忙,竟然都没注意到。
桑伦珠喊她没反应,干脆又使了点劲拉她进去,暖室中央的大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南盛点心和小菜、碗碟和杯盏。
宣卿当然能认出来,晶莹剔透的灌汤包、金黄酥脆的牡丹卷、软糯香甜的炸年糕。。。还有几壶温好的来自南盛的桂花酒酿,那香气鲜明到她一下就能闻出来。
这是把她小厨房的厨子都拉来药庭了?
丹烟、陆元君、丁太医、勃日帖和穆伦泰、那日都和宝迪都在,他们换上了红色的或有年气的衣服,正围坐在桌边,笑着看向宣卿。
宝迪满眼好奇,正和那日都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南盛的食物。
“世子妃来咯!可以开饭啦!”穆伦泰大喊。
勃日帖抬手给了他一拳,“不分场合!”他又转头看向宣卿,“本来我想带穆伦泰回去的,世子突然拦住我们。这个。。。我想了想,我们也帮了世子妃不少,吃世子一顿饭也是应该的!”
宣卿突然发现勃日帖的寒咳好了不少,说一大段也没咳一声,他坐得和丁太医很近,两人面前摆着酒杯,应该已经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有一会儿了。
“公主!”丹烟吸溜着口水喊她过去。
“嫂嫂过来坐!大哥说这是给你的惊喜,非要我瞒着你,可给我憋坏了!”桑伦珠拉着宣卿坐到丹烟旁边,和宝迪面对面,冲宝迪吐了吐舌头,她俩最是不喜欢坐在一起的。
“又去哪儿玩了!现在才来?”那日都问。
“哼,谁都跟你们一样的话嫂嫂可就丢了!只有我牵挂嫂嫂!”桑伦珠反驳,她打开红包袱,里面是一沓红包,包的是碎金子。她站起来围着桌子挨个发红包,到宝迪面前,两人手脚并用地争抢起来,谁也不让谁。
宣卿从进来就没说过话,不禁在想苏日图州出现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