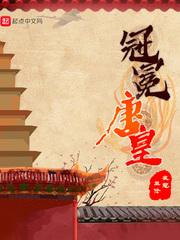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白色星尘[先婚后爱] > 2230(第21页)
2230(第21页)
听到这个称呼,时从意还是有些肝颤。
不知道是不是偷摸着领证的原因,连带着听到相关的词汇都有些莫名的偷感,也不知道这辈有没有机会习惯。
深吸一口气,她弯腰钻进后座,猝不及防对上一双深邃的眼。
席琢珩靠在后座,领带不像以往那样规整地束在领口,而是松松垮垮地挂着。
他刚从伦敦回来,身上还带着长途飞行的倦意,骨节分明的手指正按着太阳穴,却在看到她的一瞬间眸光微动。
“没好好吃饭。”他开口,声音有些哑,在封闭的车厢里显得格外低沉。
时从意下意识摸了摸脸:“吃了……”
话音未落,席琢珩突然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修长的手指圈住了她的。
“瘦了。”
他说着,的指腹带着薄茧,在她细腻的皮肤上划过时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
那触感太过鲜明,让她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席琢珩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她脸上,那双深邃的眼睛在阴影中显得格外幽深。
他的拇指在她腕间摩挲,像是在丈量她消瘦的程度,又像是在确认她的存在。
时从意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在他的指尖下加速跳动,一下比一下急促。
静了片刻,时从意才开口:“不好意思,又爽约了。”
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车窗外的车流声淹没。
“没关系。”
席琢珩淡淡应道,手握着她的,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时从意看着他略显疲惫的眉眼,目光扫过他额角那道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的伤口,斟酌了一下,“其实你不用特意来接我……”
“席太太。”他打断,那双好看的眼睛印着街灯的明灭,“还要我再说一遍提前回来的原因吗?”
他的语音低沉又清晰,带着些些不容逃避的压迫感,却又藏着只有她能听懂的温柔。
时从意顿时怔住,有什么在心底轰然炸开,碎片纷飞。
“不、不用。”
她怂的彻底。
席琢珩见状低笑一声,那笑声慵懒而磁性,像是有人用指尖轻轻拨动了她心底最隐秘的那根弦。
她记得领完证的那天晚上,他说他们是正常夫妻,说没有把结婚当儿戏。就把它当做种子埋在心里,没敢让它真正发芽。
她小心又谨慎的画地为牢,用“边界感”把自己包裹起来,不要越界不要沉溺于他的体贴和温柔,更不要对他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
甚至以为他所谓的“正常夫妻”,只是比“假结婚”多了一层体面的外壳。
可是眼前这个男人,用他风尘仆仆的疲惫,额角未愈的淡痕,紧握不放的手掌,还有此刻这声沉甸甸的“席太太”,无比清晰让她意识到,他是认真的。
他跨越山海压缩行程只为回来见她,这行为本身,就彻底颠覆了她对两人婚姻浅薄而自保的理解。
这份认知来得如此猛烈而清晰,让她心口发紧,甚至有些眩晕。
界限感在瞬间变得摇摇欲坠,恐慌和愧疚如同浪潮,席卷了她。
恐慌于自己还无法回应同等的投入,愧疚于自己长久以来的防备和疏离,更被他对这段关系所展现出的,远超她想象的认真程度所深深震撼。
两人都没再说话,狭小的空间里仿佛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
席琢珩的手始终没有松开,指腹在她腕的温度透过皮肤直抵心尖,直到停在她租住的老小区楼下。
昏黄的路灯透过银杏叶的间隙,在车顶投下斑驳的光影。
道别后时从意快步走进楼道,却在经过二楼拐角处时突然停下脚步。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头,只是鬼使神差地转身,透过积着薄灰的窗户往下望去。
那辆黑色轿车依然静静地停在原地,尾灯在夜色中泛着暗红的光,像黑夜中静静守护的萤火。
他压缩了行程风尘仆仆的来,连时差都没有倒,只为了见她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