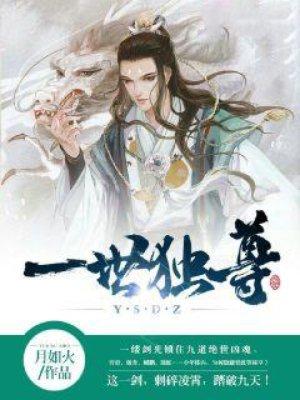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白昼边界 > Chapter 09青峡古寺(第5页)
Chapter 09青峡古寺(第5页)
他说自己上幼儿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说他没有爸爸,他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妈妈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后来念小学,懂事了,知道的也多了,得知爸爸是大英雄,总是想和其他小朋友炫耀。有一次实在没忍住,说漏嘴,被妈妈狠狠揍了一顿,从此再也不敢提自己的爸爸是大英雄了。
到了中学,他干脆接受了被外人八卦“没有爸爸”的事实,也曾为母亲不平,甚至面红耳赤地问过父亲,为什么他总是不能回家。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年时期的不理解逐渐变成了敬仰和佩服,他开始为曾经责怪父亲的言论感到自责。
直到他决定未来也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才真正明白父亲的心酸和不易。
他说:“我小时候和其他浑小子没什么区别,都淘气,还不懂事。
但是我妈特别好,她很温柔,待人也和善,父亲不回家她一句抱怨也没有。虽然小时候我半夜起床去厕所看到她房间的灯总是亮着,但她在我面前从来都是称赞父亲。我钦佩父亲的英雄气魄,可是归根结底,他欠我母亲太多。”他说着在她的眉心落下一个吻,“所以我不想重蹈覆辙,我很贪心,我要守江河,也要你开心。”
0点已经过去,山里迎接新年的氛围着实不够。
万物俱静,虞小婵在半梦半醒间只听见他说了什么“英雄”,然后就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在樱花树下。
风轻轻吹过,花瓣纷纷掉落,落在她的身边,落在她的眉间。
第二天,日晒三竿。邵颍川和怀里的小怪物还在睡。
还是门外有人敲门,虞小婵才被吵醒,蹑手蹑脚地爬下床开门。
外面阳光正好,她滑动门闩,打着哈欠把门拉开,看到面前的短发女人却愣住了。
“你找谁?”
“你是谁?”
两个人异口同声,几乎同时发问。
这个莫名其妙出现在房间门口的女人留着利落短发,眉宇之间,英气逼人。她身穿便于行动的黑色皮夹克,九分长裤和马丁靴,乍看上去比男人还要野性。
发觉短发女人的目光落在自己领口,虞小婵也警觉地低头看了一眼。
睡衣最上端的纽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衣衫不整,很难不让人想入非非。
她下意识抬手想要重新系好纽扣,却在瞄到短发女人犀利的眼风时猜出了她的身份,于是也不管胸口半遮半掩,干脆慵懒地靠在门框上,先回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邵颍川的女朋友,虞小婵。”
这个名字对短发女人来说耳熟能详,她没觉得意外:“呵,今天可算见到真人了。”
她将虞小婵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颇有些不屑:“也不过如此。”
没想到对方这么嚣张,虞小婵一个白眼翻到头顶上,退后一步,“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关门声音太大,惊动了邵颍川,等她再躺进被子里的时候,他已经醒了:“谁?”
她的小暴脾气藏都藏不住,没好气地说:“你的那位女队长找上门来了。”
“徐队?”
“嗯,眼神不好,没事找事。”她嘟囔着,翻身不想理他。
邵颍川轻笑,翻身下床,趿上拖鞋,俯身在她耳边说:“她天**怼人,媳妇大人有大量。我先出去看看,你再睡会儿。”
禅房外栽着一棵银杏树,徐轻歌就在树下,身姿笔挺。
“关键时刻,还是队长靠谱。”邵颍川感叹着走近她,发觉只有她一个人,问,“将息呢?”
徐轻歌冷着一张脸,抱臂看他:“轮到你审问我了吗?我先问你。
你离开塔图尔勒之后干吗去了?虞小婵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这一路是在工作还是在谈恋爱啊?”
邵颍川抓重点,不假思索地回答:“谈恋爱。”
徐轻歌瞪他:“再说一遍?”
他嬉皮笑脸:“谈恋爱,也没耽误工作。”
徐轻歌不想和他贫:“你能不能有点正经?”再看他衣衫不整,更生气了,“先把衣服穿好再跟我说话。”
“是!”邵颍川稍息立正,整理衣服,再抬头,恢复了往常的一本正经,认真地说,“我也不想把婵婵卷入危险之中,可是康珈认准了她是我的死穴,我不带她走,她和她的家人都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