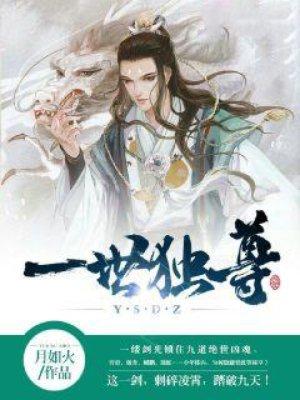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渡平城 > 4050(第25页)
4050(第25页)
内宦迎她至花厅内,当中主次分明地摆了两席酒菜,拓跋聿一身华服端坐主座,闭目养神。
冯初甫一进门,身后的雕花门窗悉数紧闭,宫婢侍从一应退了出去,阖室由着几盏铜灯渲上金。
“臣──”
“坐。”
拓跋聿打断了冯初的行礼,抬抬下巴,示意她在次席落座。
待她坐定:
“卿可否为我所用?”
突如其来的单刀直入令冯初猝不及防,她犹正色道:
“臣之心,自是向着陛下的。”
“向着朕哼”拓跋聿与往日里大相径庭,她信手拎起案上酒壶,踱步冯初案前。
白玉色的酒浆倾泻入盏,话语则在勾起冯初的愧疚:
“是向着朕,还是向着自己?”
拓跋聿在冯初身旁缓缓坐下。
随着她的动作,冯初甚至有一瞬间地紧绷腰腹。
今日的拓跋聿,竟然让她感受到了些许姑母才会带给她的威慑。
“不过不重要了。”拓跋聿端起酒盏,亲自抵在冯初唇畔,冰冷的青铜盏凉至冯初心里。
“朕与你,早已是休戚与共。”灯火在少年温良沉静的面孔下,扫出晦色阴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么?”
杏眼水汪汪的,还是那般让人心生怜爱,手腕上却使了些许气力,轻巧地撬开冯初的唇畔牙关,令她微微仰头,饮下这盏酒。
陛下在折辱她。
冯初意识到这一点后,揪紧了膝上衣裙。
她恼,却又无可奈何。
若陛下只是折辱她这一次便能释怀的话
折辱她也无妨
“卿还未回答朕。”
“自然,臣与陛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本是实话,但如此情形下说出口,实在有些怪异。
拓跋聿再度拎起酒壶,冯初怔怔地看着酒盏中渐渐涨起的酒液,呼吸不畅。
酒盏再度抵在她唇畔。
“冯初,你是不是特别害怕朕怨你?”
拓跋聿说这话时,眼眸下意识地低垂,但很快又恢复起了捉摸不定的态势。
她不能在冯初面前犹疑。
“是。”
许是问的问题太过戳人,冯初应下时,没能注意到拓跋聿转瞬即逝的犹疑。
“朕可以不怨你。”
她竟是终于肯释怀了么?
冯初这两年来愁闷的眸子罕见地粲出了光,她等着之后的条件。
刀山火海,炼狱加身,再难,也无妨!
这次拓跋聿甚至只是微微按了按手上的杯盏,冯初就顺从地张开了唇。
脖颈划出一道柔美的弧度,金镶琥珀的耳坠更是在灯火中微微摇曳。
当真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