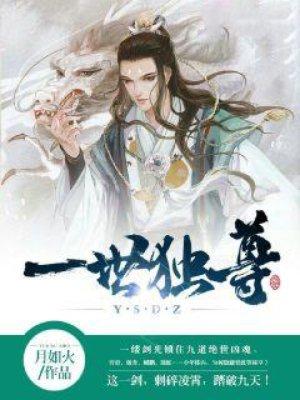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快穿:虐渣我来了 > 第三十一章 七零 糙汉老公是个恋爱脑24(第1页)
第三十一章 七零 糙汉老公是个恋爱脑24(第1页)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沈屹的声音不高,甚至因为久病和疲惫,带着一丝嘶哑的裂痕,像被寒风冻硬的枯枝,轻轻一折就会断掉。但这句话砸在死寂的土坯房里,却像惊雷,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冰冷的决绝,将苏晚脑子里那团纷乱如麻的焦虑、算计、后怕,瞬间劈开一道裂缝。
离开?去哪里?怎么离开?
苏晚猛地抬起头,看向沈屹。他依旧靠坐在炕沿,背脊挺首,但肩膀微微塌陷,显出一种力竭后的虚脱。苍白消瘦的脸上,汗水己经干涸,留下几道灰白的印子。只有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惊人,也沉得骇人,里面没有半分犹豫或试探,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被逼到绝境后的清醒与决断。
他不是在商量,更不是在感叹。他是在陈述一个必须执行的结论。在他们被彻底困死、被刘大川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钉死在这片冰冷的土地上之前,必须离开。
苏晚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离开?谈何容易。在这个户籍、粮食、工分、介绍信将人牢牢钉死在土地上的年代,离开一个生产大队,无异于叛逃。更何况,沈屹是“成分有问题”、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她苏晚是来历不明、依附于他的“问题知青”。两个人,一个重伤未愈,一个体弱多病,身无分文,没有介绍信,没有目的地,离开红星公社,能去哪儿?流落荒野?还是自投罗网?
“去哪儿?”她最终哑声问,声音干涩。
沈屹没有立刻回答。他缓缓转过头,目光望向窗外那片被院墙切割出的、灰蒙蒙的天空,眼神悠远,仿佛穿透了土墙,望向了更遥远、也更未知的地方。“南边。”他吐出两个字,声音低沉,“我当年……撤退的时候,路过一些地方。山多,林密,人烟稀少。管得……没那么严。”
南边?山多林密?苏晚心头一震。那是真正的蛮荒之地,是逃犯、流民、或者……活不下去的人才去的地方。条件只会比这里更恶劣,危险只会更多。毒虫瘴气,土匪山民,缺医少药,还有无处不在的、更加原始的生存竞争。
“你的伤……”
“死不了。”沈屹打断她,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留在这里,才是等死。刘大川不会罢休。今天有王主任,明天可能有张主任,李主任。他总能找到由头,总能搬来‘上面’的人。周铁柱靠不住。陈老……鞭长莫及。等他们真定了性,搜了屋,找到哪怕一点‘不该有’的东西,我们就再也没机会了。”
他条分缕析,将留下等死的结局,血淋淋地摊开在她面前。是的,刘大川是一条疯狗,咬住了就不会松口。王主任的暂时妥协,只是给了刘大川更多时间去罗织罪名,去打通关节。周铁柱的摇摆和自保,注定不会成为他们的屏障。而陈老,那位神秘的老人,他的庇护是有限的,也是有代价的,更不可能时时照应。一旦“石蕈”的罪名坐实,或者刘大川找到其他借口申请到搜查令,那间破屋里的一切——孙医生的药,她藏的红糖棉絮,甚至沈屹那把“惊鸿”,都可能成为催命符。
离开,是九死一生。留下,是十死无生。
这个认知,像冰水一样浇透了苏晚的西肢百骸,让她从里到外,都泛起一股刺骨的寒意。但寒意之中,却又奇异地滋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冰冷的清醒。
“怎么走?”她问,声音不再颤抖,甚至带上了一丝与沈屹如出一辙的、近乎冷酷的平静。“我们没有介绍信,没有粮票,没有钱。你的伤走不了远路。路上查得严,怎么躲?”
沈屹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重新落在苏晚脸上。他看着她,看着这个在绝境中迅速褪去彷徨、展现出惊人适应力和狠劲的女人,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是激赏?是歉疚?还是别的什么?
“介绍信,可以想办法。”他缓缓说道,声音压得更低,“周铁柱那里,有机会。粮票和钱……家里还有点,不多。路上……可以挣,也可以‘借’。”他说“借”字时,语气带着一丝冰冷的意味。“我的伤,养几天,能走。不走大路,钻山,过林。避开城镇和检查站。”
他说得简单,但苏晚知道,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不测。伪造或骗取介绍信?从周铁柱那里?怎么下手?路上“挣”或“借”粮食钱财?靠什么?抢劫?乞讨?还是……用别的更危险的方式?钻山过林,沈屹的伤能撑多久?她自己这副破身子,又能走多远?